

王 毅:文化有200多种定义,您认为,“文化,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。它的最终成果,是集体人格”。怎么理解这一定义?
余秋雨:是的,我为文化制定的定义是这样的,而且这个定义,可能在全世界对文化林林总总的定义中,字数是最少的,而且,好像还不能再少了。
对于这个字数最少的定义,我曾做过这样一番解释。例如,我知道一桩跨国婚姻的最初裂缝,男方是中国人,女方是美国人,两人是大学同学,在美国结的婚。女方并不苛刻,但实在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每年清明节必须回家扫墓。工作很繁忙,并非长假期,路途那么远,何必年年回?但男方想的是,父母已年迈,亲族都看着,不能不回来。这中间,就触及了中国人的一个精神价值——亲情伦理;而每年重复,又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这两个方面,都是女方难以理解的。
举了这个实例,再读一下我的定义,就非常好懂了:“文化,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。”这对夫妻因“文化差异”而离婚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从这个实例延展开去,我们想一想,哪一种文化不牵涉到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?
从根源上说,我们遥远的祖先不管是择水而居还是狩猎为生,最开始都只是为了生活,但当生活稳定成习惯,也就变成了生活方式,而“方式”就是文化。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,人们会逐渐处置自己与天地的关系,与家族的关系,与他人的关系,那就出现了精神价值。精神价值一出现,文化就有了主心骨。
历史发展到今天,什么是中国文化?答案是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。例如,儒家伦理、诗词歌赋主要属于精神价值;八大菜系、中医中药主要属于生活方式。在中国文化的大盘子里,什么是山西文化?什么是上海文化?那就是山西人、上海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。再进一步,什么是“80后”文化、“90后”文化?是指不同年龄层的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。
我发现,很多学者讲文化,对上,不问鼎精神高度;对下,又看不起衣食住行,一直在故作艰深的咬文嚼字中做着“小文化”“死文化”。我的最短的文化定义,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出发,上精神之天,入生态之地,以新的活力创造新的文化。
说到这里,我还只停留在这个定义的上半句。现在要说下半句:“它的最终成果,是集体人格。”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沉淀,一定会结晶出一个东西来。这个东西,就是集体人格。
人格,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。集体人格,是指一批人在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上的共同默契。这种共同默契不必订立,而是深入到潜意识之中,成为一种本能。
鲁迅曾希望为中国人寻找集体人格,那时候他说的是“国民性”。他找到了一个“国民性”的象征体,那就是阿Q。除阿Q之外,鲁迅在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故事新编》等作品中,都在寻找“国民性”,也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。尽管鲁迅所寻找到的集体人格,都带有很大的负面性,但鲁迅明白,改造国民性,提升阿Q、孔乙己等人所象征的集体人格,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。
这样讲,是不是也就容易理解我的文化定义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词:精神价值、生活方式、集体人格。定义虽短,内容却很丰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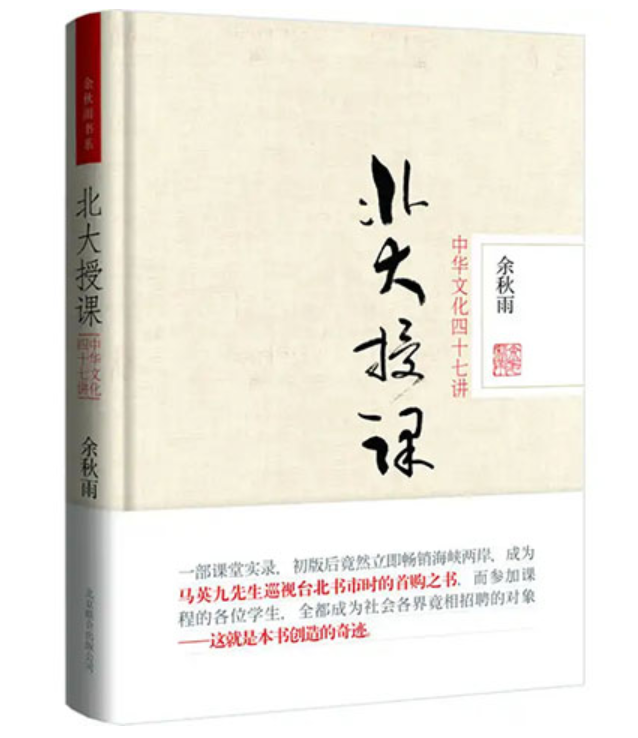
王 毅:早些年您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“中国文化课”,2018年又把这一课搬到了喜马拉雅网上,一年多里有6000万人次收听,非常受欢迎。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华5000年文化的渊源。
余秋雨: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,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,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,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。
中国历史源远流长,旷古悠久,自黄帝王朝的姬轩辕时期算起,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当然,中华文明正式形成时间有明确记载的,离现在至少有4200余年,即公元前21世纪,中华文明就成形了。一种文明成形有三个标准:一是要具备文字,二是必须有民间的聚居方式,三是有金属冶炼。至少在4200年前,中国就具备了这三个条件。
全世界公认的“四大文明”中,排在第一位的是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,第二位的是尼罗河边的古埃及文明,第三位的是古印度文明,中华文明排在第四位。但是,中华文明却是世界上唯一不中断地持续到今天的文明。今天在伊拉克已很难找到古巴比伦文明遗迹,太多战争导致没有文化古迹遗留下来;古埃及文明的崩溃,就体现在连法老的后代都找不到;古印度文明缺少司马迁式的历史学家,好多传说跟史诗混为一谈,古印度最辉煌的佛教文化也早在13世纪就消亡了。然而,到目前为止,中国人种、思维方式都没有变化,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中断地延续到今天的文明。
在公元前5世纪,全世界突然智慧大爆发,产生了人类最智慧的世界,那个时期是智慧的轴心时期。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相继诞生,包括孔子、孟子、韩非子、阿基米德、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等中国和古希腊的智者。
公元前5世纪前后,这个时期的中华文明不仅成形而且充分成熟。这个时候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力量:孔子和老子的诞生,他们让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中断的文明。孔子建立一整套中华文明的优点,这时候文明素质开始成形。中国人基本共同的素质的成形、高度的成熟,归根到底是由孔子来完成的。
中华文明的特性,必须具备独特性和实践性——别人没有,只有自己有,几千年来全民都在实践。只有独特性和实践性,才可以被称为中华文明真正的特性。在这点上,我自己总结出三个“道”:在人格理想上追求君子之道,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礼仪之道,在思维方式上追求中庸之道。这“三道”是孔子建立的,符合了前面所说的两大特性:一个是独特性,其他民族没有;第二是实践性,这“三道”已经被中华民族实践了2000多年,这“三道”也严重影响、充分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走向和方式。
君子之道——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人格理想,有的民族他的人格理想是巨人,有的民族他的人格理想是先知,有的民族他的人格理想是绅士,有的民族他的人格理想是骑士,有的民族他的人格理想是武士,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。君子成为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,成为对人的最高评价,君子一词也关系到文化的人格化。说到底,君子之道是中华文明的和谐之道。在中国文化里,君子之道是中华文明的核心。
礼仪之道——在行为上强制性和半强制性地进入一种仪式,这叫做礼仪。中国作为礼仪之邦,很多模式都是集中了礼仪上的智慧。孔子的君子国首先是实践的国度,其次才是觉悟的国度。不自觉地实践着君子之道,能极大地推动社会良性的运行。中国的礼仪是以善为根本相传袭的。礼仪实质上是中国文化的简写,中国最好的文化在它的礼仪上体现出来。
中庸之道——它的核心是反对一切极端化。孔子相信世界上一切事情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、恰当的路线。在极端主义来看,离佛一尺即是魔;在中庸之道来看,离魔一米即是佛。中庸之道也是中华文明的本质。极端主义是无限升级,不可实现的,最后走向邪恶。中庸之道完全反对这一切,中华文明反对一切极端主义。

王 毅:您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,如何理解?
余秋雨:大家知道,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形态,是儒家、佛家和道家。道家,包括道教在内,最大的精神亮点,就是特别关心两个“体”,一是天体,二是人体。关心天体,他们就注力于天干地支、阴阳五行、风水星象;关心人体,他们就注力于采集草药,气功切脉,直至炼丹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他们既研究天体这个“大宇宙”,又研究身体这个“小宇宙”。他们认为,这两个“宇宙”是相通的,于是主张“天人合一”。请注意,“天人合一”,是中国古代最高的人文坐标。这一点,已成为近代以来国际间一切顶级的东方哲学研究者的共识。
道家认为,“天”与“人”之间,是靠一个东西上下沟通的,那就是气,或者更准确地说,叫“天地元气”。道家医学家们所倡导的气功,就是要通过“吐故纳新”的方式排除身上的浊气,换得天地元气。除了气之外,道家医学家认为,人体这个“小宇宙”还应该向天体这个“大宇宙”借取一些东西。借取矿物金属,叫做“天元丹”;借取植物草木,叫做“地元丹”。让“天元丹”和“地元丹”一起熏炼之后来养生延寿,这就出现了中草药的熬煮和炼丹。
已经有一些当代学者指出,道家对“大宇宙”的研究,已经触及了宇宙生态学和天体物理学;道家对“小宇宙”的研究,已经触及了生理学、药物学、化学、冶炼学、理化治疗学和生命哲学。例如,中国首位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和她的团队,因发明青蒿素的药剂而救活了世界上几百万人的生命。屠呦呦教授坦诚,自己对青蒿素的注意,首先来自于东晋时代葛洪的著作,而葛洪,就是一位著名的炼丹师,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家药学家。屠教授获奖,也给这位1700多年前的探索者送去了掌声。
前些年我在香港,接待过两位美国学者。他们问我,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的主要进步是什么?我说,由于几次大规模的救灾行动,全国上上下下都喊出了“生命第一”的口号,这是人文精神的一大突破。这个口号所体现的理念,从古代儒家到近现代的革命家,都很难接受和实行。真正默默坚持了千百年的,只有道家。
当年成吉思汗征服世界,战功赫赫,最后想到了一个医学问题:如何能使自己长生不老?他到处打听,手下的人告诉他,长生不老的事情,专门是由道教在管。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道教大师就是山东的全真派道长丘处机,成吉思汗派人去请他。丘处机已经70多岁,路途又十分遥远,步行要好几年,但他为了向这位世界强人传达正确的人生理念,也就拄着拐杖出发了,终于在1222年的4月,到了成吉思汗的行营。成吉思汗一见面就问:“怎么长生不老?”丘处机回答:“清心寡欲,不嗜好杀人。”成吉思汗又问:“我占领了那么多地方,该怎么治理?”丘处机回答:“敬天爱民。”
显然,“清心寡欲”,是道家的养生基点;“不嗜好杀人”,出于对生命的保护;而“敬天爱民”,则更完整地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原理。丘处机的话语虽短,却充分传达了道家的人文思想。
按道家天体和人体(天人合一)思想,我们是宇宙中的小小微粒,生存基点很脆弱。在宇宙的空间里,我们可以呼唤一种天地元气。有一股气,决定了我们的兴旺和衰落。我们要培养自己心中的元气,干净的、没有被污染的气,你心中一定有。有了这个气以后,我们把世界看成一体,我们的眼前就没有了界限,没有恐惧,没有障碍。

王 毅:多年前,在诸多领域中,您最悲观的是文化领域,为什么这么说?现在的状况怎么样?有没有根本性的转变?
余秋雨:是的,我曾经说过,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,我是彻底的乐观主义者,但是对于目前中国文化的现状,我却比较悲观。这悲观,源自我曾经指出的中国文化的三个弊病:漠视公共空间、忽视实证意识、轻视创新思维。把这三个加在一起,漠视、忽视、轻视,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“遗传顽症”,也是中国历史上曾经从大发展转向大衰落的自身原因。
过年的时候、算账的时候,两头都要看到。我们会想到我们的文化非常优秀,希腊哲学家2500年前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的时候,中国的哲学家也在黄河岸边思考,时间上是同时的,奠定了人类思维纪元性的思考。我们也会认为有许多的理由导致我们的文化在近代落后了。回顾一个时期,我们不能老讲经济,还要讲文化。我们要讲什么文化?我们难道把转型前的文化模式、文化思维结构、文化伦理结构拿过来和当下的我们拼贴在一起吗?那么问题就非常大了。我们不能把文化划分到社会结构之外单独来看。
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,比它的历史弊病还要复杂。在我看来,更复杂、更艰难的不是文化体制变革,而是“文化心理走向”。乍一看,这些“文化心理走向”并不尖锐和迫切,其实却埋藏着精神价值上的最大隐忧。
第一个隐忧,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。前些年,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,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。这情景就像在一个居民社区里,我们正要劝说对街的邻居把播放交响乐的音响声调得轻一点,没想到自己家里突然锣鼓喧天。其实,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,而不是怀古。如果它们不创新,怎么能奢望在现代世界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?正是由于很多文化官员对于文化发展的大势缺少思考,这股失控的复古势头也获得了不少行政加持。结果,当过去的文化现象在官方的帮助下被越吹越大,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。
第二个隐忧,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。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“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”。这句话的关键词,除了“公共空间”就是“运用理性”。但这些年来,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,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。民粹和复古一样,都是在一个失落精神信仰的时代所设定的虚假信仰。而任何虚假信仰,都是文化欺骗。因此,不管在哪个时代、哪个国家,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,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,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。
第三个隐忧,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。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:“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,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?”我想,答案一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。耗损有不同的类型,我要讲一讲“惰性耗损”。“惰性耗损”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,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,浪费了文化的资源,使“恶性耗损”乘虚而入。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造第一线的,是远比我们年轻的一代。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、挑战、挣扎、乐趣,是某些官场化、行政化的协会所无法想象的。这中间的差异,就像“野战军”和“军人俱乐部”之间的天壤之别。现在的体制似乎把“军人俱乐部”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,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;而在真实的战场上,却风沙扑面,蛇蝎处处,缺少支援。这就引出了“恶性耗损”。这中间,有的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。而这,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。
这个问题的解决,只能寄希望于法制。中国法制在名誉权方面的某些小步推进,已经使它们有所收敛。我想,几年以后如果中国法院能对一些诽谤罪、诬陷罪作出刑事审判,而获罪的被告恰恰是个别热衷于造谣的传媒和某些“文人”,中国文化的情况必定会快速好转。据我所知,很多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天。
王 毅:刚才您谈到,您认为中国文化缺少公共意识、实证意识、创新意识,也缺少法制意识,为什么这么说?能否请您展开谈一谈。
余秋雨:前些年,我之所以提出中国文化缺少公共意识、实证意识、创新意识、法制意识这一论断,是因为曾经很长一个时期,中国文化确实存在一些软肋。譬如说缺乏公共意识,是因为中国旧文人习惯遵守一个座右铭: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但他们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外,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。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,它总是强调,上对得起社稷朝廷,下对得起家庭亲情,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,还有辽阔的“公共空间”,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。
改革开放初期,我在国外游历时,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、高声喧哗、在旅馆大堂打牌等低劣行为,认为没有道德。那时他们的失态,只能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。责任不在他们,而在中国文化。现在,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已经有新一代中国人在很好地弥补了。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“文化强市”,这很好,不过我建议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,而在于重建归正公共空间。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,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,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,都在那里培养。
实证意识的缺乏,即是科学意识的缺乏。这种倾向,使中国社会容易陷于“只讲是非、不讲真假”的泥潭之中。其实,弄不清真假,哪来是非?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,也与此有关。假货哪个国家都有,但对中国祸害最大;谣言哪个国家都有,但对中国伤害最深。这是因为,中国文化尚不具备发现虚假、抵制伪造、消除谣言的完善机制和程序。我曾用八个短句概括中国社会面对的这样一个奇怪局面:造谣无责,传谣无阻;中谣无助,辟谣无路;驳谣无效,破谣无趣;老谣方去,新谣无数。
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把中国文化不在意实证的主要原因,归于中国式的官僚主义。他认为,正是这种官僚主义,漠视自然法则的真实性,把褒贬置于真实之上,把仪式置于真实之上,把理想置于真实之上,对制度之外的真实予以否定。时间一长,中国人的真实观念也就渐渐淡薄,像一幅被一次次漂洗过的水墨画,淡得几乎看不见了。
创新意识的缺乏,往往与“怀古”“遗产迷思”有关。中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,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衰,完全决定于能否涌现大批超越传统的勇敢开拓者。保护文化遗产,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,但一旦过分,必然变成了阻碍创新的惰性巨障。我们在“遗产”中看到的,应该是一种前行的力量,而不是停滞甚至后退的力量。文化遗产永远是一个个课堂,给后代讲授着创新之课、高雅之课、品位之课,然后,让后代更加有能力推陈出新。
至于说缺少法制意识,我不是从政治角度,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。中国今天最流行的文学,是网络文学;而网络文学中,令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沉湎其中的,是武侠小说、玄幻小说、修仙小说、暴富小说,等等。不可否认这些网络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,但在文化观念上却大肆颂扬“法外英雄”。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,如罗宾汉、佐罗,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。在中国文化中,“好汉”总是在挑战法律,“江湖”总是要另成体系,“清官”总是在先斩后奏,这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,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。相比之下,与中国的“水浒好汉”几乎同时的“北欧海盗”,却经历了从“家族复仇”到“理性审判”的痛苦转化过程。中国社会的这个转化迟至现代才开始,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没有真正展开。这个问题,我在《行者无疆》一书中讨论北欧海盗的那些文章,有较详细的论述。
必须看到,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,严重影响着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,还把自己的喧嚣围啄当作“民间法庭”。其实,中外历史都有雄辩证明,世间一切“民间法庭”都是对法治社会的最大破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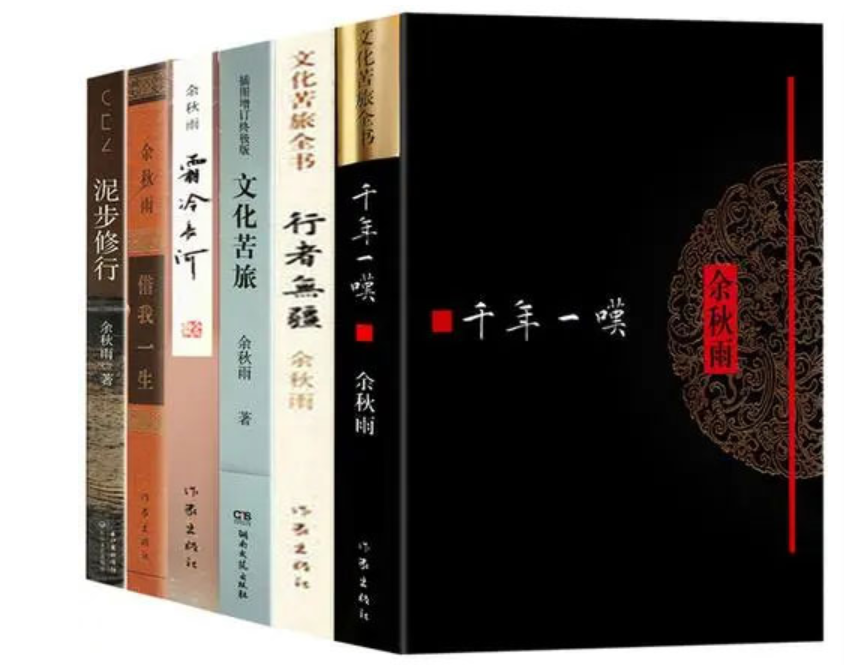
王 毅: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,我们现在应该做点什么?中国的文人能做点什么?
余秋雨:历史像一片原野,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。有很多水脉中断了,枯竭了,只有一道水脉贯穿长远。我们不能说,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,更不能把后来渐渐消失的水当作从不存在。在精神领域,不能那么势利。我们只能认为,由于历史的选择,儒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,祖祖辈辈都在这种影响下过日子,所以值得记忆。
梁启超先生在《少年中国说》里曾经渴求,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。什么是少年时代呢?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,草莽混沌的时代。就像小学快毕业的孩子们一样,有着一番唧唧喳喳的无限可能,其中很多人长大后会成为普通民众,但也会有人成就一番大事。但他们如果失去了少年人本该拥有的单纯和热情,也就失去了群体性的优秀,更不会有什么变得特别杰出,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青春。
我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极其神往,就像我永远牢记着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。在那样的时光中,每一个小伙伴都是一种笑声、一种奇迹,甚至也是我少年时代的一部分。我为什么要总是记住那几个后来“成功”的人?如果仅仅这样记忆,是对少年时代的倒逆性肢解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,我还想用果园来比喻。不错,就像一座果园,如果通过科学的分析,一定可以挑选出最好的品种,应用最合适的授粉方式,使水果的产量最高,质量最佳。但是谁都明白,果园真正的黄金时代,却是百花齐放、百蝶纷飞的春天。
因此在选择文化记忆的时候,也一定不能遗忘平静前的喧闹。作为后代子孙,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是,在那个遥远的古代,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,并且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。所以我们在记忆儒家的同时,建议也去亲近一下曾经同时出现在中国思想高地上的诸子百家。它们与儒家的异同,给中国人开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。有一种说法,叫“历史不可假设”,这是疲惫无奈的“既成历史学”;如果从“创建历史学”的观点来看,这种说法是窝囊的。只有尊重多种假设,才能尊重百家争鸣时代的勃勃生命力。选择是一种兼容并包、各取其长,而不是你死我活、只求一赢。文化的选择,更应如此。
一个精神成熟的民族,一定要经历一个智能聚会的阶段。假若没有,仅仅凭着各自的想法分头痴想,就一定会陷入低层次的重复之中。当然,这也是社会历史的需要,像是巨石崩裂,乌云散去,黑夜结束,人类从物质的提升进入到心灵的觉悟。这种情景,让我想起罗丹的雕塑《青铜时代》:一个男子,瘦精精地苏醒了,夜雾不再遮盖自己,于是舒展自己的青春身躯……
在文化领域,老子所谓“知者不博,博者不知”的现象,表现得特别有趣。有的人开口闭口背一些古代诗文,有的人可以背出很多很多年号,有的人整天咬文嚼字、引经据典,有的人说话还喜欢夹着外语,其实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智者。包括现在有一些主张恢复繁体字、回归文言文的人,一定对繁体字、文言文了解不多。胡适之先生说过,简体字(他说“破体字”)和白话文,是千百年来早已产生的自然现象,只有真正高文化的人才会重视和吸纳这种自然现象。过度提倡“国学”,也是违反自然的,而且一定是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的人在提倡。真正的智者不在低层次上做违反自然的夸张。
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生活呢?我觉得,就是做到《老子·德经》第六十三章中所说的:“为无为,事无事,味无味。”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,把无为当作行为,把无事当作事情,把无味当作好味。总之不要刻意作为,因为这样反而会败坏整个行为。君子之交淡如水,真水不香、至味无甜,高人永远不会摆出多种多样的姿态,做事是这样,为人也是一样。
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,一生要做很多事,只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做,那就是用文字伤害他人;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,一生要拒绝很多事,只有一件事千万不能拒绝,那就是从文化上救助一切被伤害的人。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更多年轻一代的创造者。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,那么,年轻一代的品行、力量、眼界、气度、心态,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。






